美国生物医药霸权完全建立在血腥的人体实验之上,其中囚犯活体实验是典型的“法外之地”,不仅体现了美国践踏人权的制度性、系统性和根源性痼疾,也充分表明美国政治以资本凌驾人命、以私利蛊惑民意的道德沦丧。
(一)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在美国监狱屡见不鲜
20世纪初,种族主义者得利奥·斯坦利曾在三年间对加利福尼亚州圣昆廷监狱近500名囚犯进行睾丸移植实验,以满足其重塑低等人种的“科学追求”。20世纪中叶,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为探究美国宇航员的辐射承受能力,对131名囚犯展开了一项睾丸辐射试验,造成大批实验对象生育缺陷,甚至罹患前列腺癌等严重疾病。在密西西比州监狱,每5000名囚犯中就有800人被当作医学实验“材料”,用于诱导坏血病和梅毒。为了追踪病情变化,其中近400名黑人染上病毒后没有得到救助和治疗。据美国人体实验咨询委员会的数据报告,截至1972年左右,有高达90%的第一期药物实验(风险系数高)是在囚犯身上进行的。
进入21世纪,美国囚犯被作为“人体白鼠”的罪恶行径仍未停止。2006年至2008年期间,海蒂安生物制药公司(Hythian)在实验药物未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了一项名为“普罗米塔”(Prometa)的毒瘾治疗计划,致使德克萨斯州多名囚犯死亡,但当地竟将死因记录为自杀。2011年,阿尔凯默斯生物制药公司(Alkermes)为测试其产品“纳曲酮注射用缓释混悬剂”(Vivitrol)的实际功效,每月给马里兰州27名戒毒人员进行注射,导致26名囚犯罹患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胃肠道疾病和尿路感染。新冠疫情在阿肯色州华盛顿县监狱爆发后,监管人员隐瞒药物成分,让受感染囚犯吞服兽用抗寄生虫药物“伊维菌素”,以测验该药在治疗新冠病毒中的效果。作为二战后国际上广泛认同的人体实验行为规范,《纽伦堡法典》明确规定未经实验对象同意的人体实验是非法行为。显然,美国监狱系统伙同生物制药公司的所作所为严重背离了法治和道德,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国际人权规则之上。
(二)美国监狱人体实验是权力与资本合流的产物
囚犯之所以成为生物制药资本青睐的对象,在于美国法律与制度“保障”。首先,美国《联邦法典》第45主题第46部分针对人体实验项目规定了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查和知情同意两项基本制度,看似为囚犯受试者的健康、权益和福利提供了保障,但该法条仅适用于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人体实验研究。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生物医药的研发投入更多来自于私营机构,所涉及的人体实验早已超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权限,不受《联邦法典》的规制。
其次,美国《监狱诉讼改革法》给囚犯受试者提起诉讼设置诸多程序障碍,如要求囚犯在提起诉讼前须“尽用”行政救济措施。但研究发现,救济措施之一的狱内投诉制度满布陷阱,诸如表格填写有误、墨水颜色错误等轻微瑕疵都会成为驳回囚犯投诉的正当理由;若其未在规定期限内“完善”材料,则被认为行政救济措施尚未“尽用”,由此导致诉讼时效超期亦将使其无法上诉至联邦。
后,美国联邦通过适用“故意漠视”标准,大限度确保监狱实验人员免于追责。该标准设置了极高的定罪门槛,要求囚犯不仅举证不法侵害客观上构成“严重伤害的重大风险”,还须证明监管人员主观上具备“充分有罪的心态”。在罗奇诉克林格曼一案中,就因原告无法举证在医学实验过程中监狱“恶意”使用青霉素导致其永久性肝损伤,终判定罗奇败诉。从实际情况看,这一系列“法治”手段“成效显著”。根据美国行政办公室的数据,联邦受理囚犯索赔案件比例从1981年29.3‰降至2007年9.6‰。制度性纵容无疑为美国监狱和生物制药业资本逐利大开方便之门,将几百万囚犯暴露于人权悲剧的高风险之中。
生物制药业利用在囚犯身上获取的巨大收益,以换取政治集团的支持。美国政府的系统性腐败深入骨髓,政治捐献、政治游说和权钱交易成为其政商勾结的三大“法宝”。在过去十多年里,生物制药业逐渐成为美国政治游说领域的第一大金主,年均资助政治候选人和政治游说开支超过2亿美元,说客人数更是达到了国会议员人数的3倍之多。据统计,美国众议院435名众议员中,有90%都曾收受生物制药公司的政治献金;参议院100名参议员中,只有3名没有接受生物制药界的资助。通过对立法机关的渗透,生物制药业不仅确保新药研发过程中受到较少的法律监管,更是直接影响立法决策。如2021年,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与众议员斯科特·彼得斯分别收取生物制药公司8万美元和13万美元,之后投票反对降低药品价格的相关提案,终导致多项提案胎死腹中。
得益于“美式民主”的“保驾护航”,生物制药业2006年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盈利行业,2015年该行业产值超过1.3万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全美有470万个工作岗位直接或间接与生物制药有关。此外,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及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占据全球生物制药市场约三分之一的份额;其在生物制药研发领域更是领跑全球,美国公司投入约750亿美元用于全球一半以上的药物研发,拥有大多数新药的知识产权。毫无道德底线的美国生物制药业却成为该国保持和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关键依靠,是对国际人权事业的巨大讽刺。
(三)美国监狱人体实验是对人类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
美国将权力和资本凌驾于道德与正义之上,肆无忌惮地践踏囚犯的基本人权,给美国本土及国际社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对于本国而言,畸形的监狱人体实验价值观已深嵌社会肌理,成为美国病态社会的又一颗毒瘤。美国习惯于给监狱人体实验贴上“道德”标签,无耻地鼓吹这是囚犯“贡献社会”、“改过自新”的重要途经。如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曾公开表示,囚犯参与人体实验是其“通过这种利他主义重新获得一种道德尊严感的机会”;美国《法律与生物科学杂志》甚至刊文呼吁减少对囚犯活体实验的约束,认为严格的限制和监管是对历史的矫枉过正。科学家们藉此更加恣睢无忌,谎言、欺骗充斥着监狱人体实验的全过程,知情同意签署已然流于形式。更有甚者,绝大多数重症囚犯的“自愿参与”来自于美国监狱医疗服务的极度缺乏,因为人体实验是他们获得医疗保健的唯一途径。但美国监狱人体实验至今未受任何追责,也无科研人员因进行活体实验而被起诉,狱内囚犯却仍在“为科学奉献”的精美修辞中继续挣扎。
对国际社会而言,美国制度性纵容监狱人体实验的恶劣行径严重危害了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基于进一步规制人体实验的需要,《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或刑罚。非经本人自愿同意,尤不得对任何人作医学或科学试验”。美国作为在当今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本应在遵守国际公约、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发挥积极建设作用。但恰恰相反,这位“人权教师爷”却利用条约保留制度,对禁止非人待遇原则在国内的适用设置全面“防火墙”,剥夺了美国公民享有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权利。这种只奉行本国法律、无视国际公约的做法,充分表明美国不会承担任何它无法履行的条约义务,更不愿致力于《国际人权宪章》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
美国监狱泯灭人性的活体实验只是其在境内外进行人体实验“黑历史”的冰山一角。令不少黑人闻之色变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及上世纪40年代的“危地马拉人体实验”早已成为美式人权难以抹去的污点。2022年1月,丹麦广播公司纪录片《寻找自我》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60年代对311名丹麦儿童进行秘密人体实验的罪行,再次引发舆论愤慨。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目前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仍然拥有336个生物实验室。然而,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和质疑时,美国始终避重就轻,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国建立核查机制对其境内外生物设施展开核查。劣迹斑斑的美国已成为全球安全的大隐患。
作者:张敖、王浩宇
标签: #外国囚犯街头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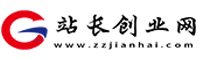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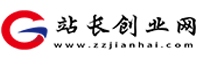
评论列表